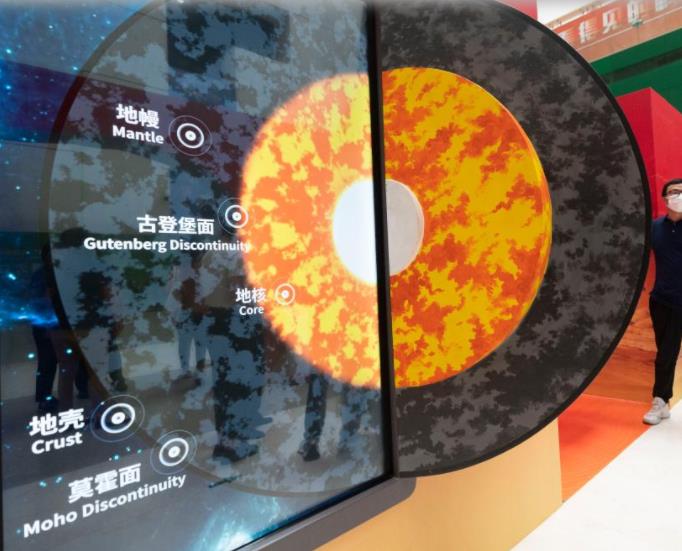來源:人民(mín)日報海外版
孫犁青年時期即以《荷花(huā)澱》成名(míng),但并未大紅大紫;中(zhōng)年生病,封筆(bǐ)二十餘載;晚年筆(bǐ)耕于“芸齋”,崇尚“人淡如菊”。青年孫犁和晚年孫犁創作(zuò)旨趣大有(yǒu)不同,故以“清荷”“淡菊”兩種風格名(míng)之。以往研究者更多(duō)把目光投向青年孫犁,關注他(tā)作(zuò)品中(zhōng)主題的獨特和叙述的詩意,即“清荷”一面。新(xīn)世紀以來,孫犁研究明顯發生兩個轉向,一是更為(wèi)關注晚年孫犁的“淡菊”風格,二是建構整體(tǐ)孫犁,闡發兩個階段之間的關系。受各種因素影響,海外對孫犁的評價與國(guó)内并不同步。通過對照青年孫犁、晚年孫犁兩個創作(zuò)階段,可(kě)以看出其海外譯介的情況及特點。
被廣泛譯介的青年孫犁
青年孫犁時期,指孫犁上世紀30年代開始寫作(zuò)到上世紀60年代初擱筆(bǐ)。這一時期,對孫犁作(zuò)品的翻譯和介紹已經開始。上世紀50年代初,孫犁屬于被重點培養的青年作(zuò)家。1951年底,孫犁參加了訪問蘇聯的中(zhōng)國(guó)作(zuò)家代表團,同行者有(yǒu)柳青、魏巍、李季、康濯、徐光耀等,都是文(wén)壇青年才俊。作(zuò)家代表團由馮雪(xuě)峰任團長(cháng),一個多(duō)月時間内訪問了莫斯科(kē)等地,參加多(duō)項文(wén)學(xué)活動,受到蘇聯作(zuò)協熱情招待,擴大了中(zhōng)國(guó)作(zuò)家在蘇聯的影響。孫犁由此走向了“世界”,近距離體(tǐ)驗了蘇俄文(wén)學(xué)生态,回國(guó)後寫了多(duō)篇訪蘇紀實。
上世紀50年代,中(zhōng)國(guó)積極向海外推介優秀文(wén)學(xué)作(zuò)品。古典文(wén)學(xué)、現代文(wén)學(xué)的佳作(zuò),被精(jīng)心挑選後,成規模地譯出。1951年,外文(wén)局創辦(bàn)了《中(zhōng)國(guó)文(wén)學(xué)》,以叢刊形式定期出版,有(yǒu)計劃地進行外譯工(gōng)作(zuò),成為(wèi)展示中(zhōng)國(guó)文(wén)學(xué)的重要窗口。《中(zhōng)國(guó)文(wén)學(xué)作(zuò)品英譯本索引手冊》(胡志(zhì)揮編,譯林出版社1993年版)中(zhōng)的很(hěn)多(duō)作(zuò)品,就來自《中(zhōng)國(guó)文(wén)學(xué)》。孫犁小(xiǎo)說頗受《中(zhōng)國(guó)文(wén)學(xué)》關注。1961年,《中(zhōng)國(guó)文(wén)學(xué)》發表了《鐵木(mù)前傳》。1964年,發表了《孫犁小(xiǎo)說選》,收錄《吳召兒》《丈夫》。1966年,發表了《村歌》。其時,翻譯家戴乃叠正處于活躍期,将多(duō)部孫犁作(zuò)品譯出,推薦給國(guó)外讀者。1962年,戴乃叠翻譯了孫犁的《山(shān)地回憶》和《蘆花(huā)蕩》,發表于《中(zhōng)國(guó)文(wén)學(xué)》第9期。《風雲初記》片段發表于《中(zhōng)國(guó)文(wén)學(xué)》1963年第9期;《光榮》發表于1965年第10期。由此可(kě)見,“青年孫犁”被翻譯推介的頻率很(hěn)高。
這些被選中(zhōng)的孫犁作(zuò)品,既屬于革命曆史叙事,又(yòu)具(jù)有(yǒu)較高的文(wén)學(xué)性。孫犁的辨識度在于,他(tā)參與了以豪邁、粗犷為(wèi)美學(xué)底色的革命叙事洪流,又(yòu)具(jù)有(yǒu)獨特的個人視角,顯現出柔美、克制的“清荷”風格。在硝煙炮火中(zhōng),他(tā)聞到了荷花(huā)澱飄來的陣陣花(huā)香。正如《荷花(huā)澱》中(zhōng)的經典描寫:“這女人編着席。不久在她的身子下面,就編成了一大片。她像坐(zuò)在一片潔白的雲彩上。她有(yǒu)時望望澱裏,澱裏也是一片銀白世界。水面籠起一層薄薄透明的霧,風吹過來,帶着新(xīn)鮮的荷葉荷花(huā)香。”這類在革命曆史題材中(zhōng)獨樹一幟的作(zuò)品,符合《中(zhōng)國(guó)文(wén)學(xué)》的定位,大概也是孫犁受到遴選者青睐的原因。
上世紀六七十年代,一些海外研究者将孫犁作(zuò)品劃入抗日小(xiǎo)說的範疇,而在這個框架中(zhōng),孫犁作(zuò)品的獨特性被忽略,比如美國(guó)學(xué)者夏志(zhì)清就沒有(yǒu)在他(tā)的《中(zhōng)國(guó)現代小(xiǎo)說史》中(zhōng)提及孫犁及其作(zuò)品。其對革命作(zuò)家的态度,受到了捷克斯洛伐克漢學(xué)家普實克的批評,後者給予解放區(qū)文(wén)學(xué)很(hěn)高評價,認為(wèi)“發生在解放區(qū)生活各個方面的種種變遷,也許是中(zhōng)國(guó)人民(mín)曆史上最光輝的一頁(yè)”。整體(tǐ)來看,冷戰時期的研究者還未能(néng)認識到孫犁作(zuò)品的獨特價值。
上世紀70年代末,孫犁重返文(wén)壇,出版了《芸齋小(xiǎo)說》及大量散文(wén)。晚年孫犁可(kě)謂“衰年變法”,知人論世,都與此前的“清荷”風格不同,形成獨立傲岸的“淡菊”風格。如何分(fēn)辨、統一兩者間的關系,成為(wèi)研究者關注的問題。學(xué)者楊聯芬在1998年的論文(wén)中(zhōng),将孫犁定位為(wèi)“革命作(zuò)家中(zhōng)的‘多(duō)餘人’”,不再把孫犁框定在傳統的叙述範疇,而是發掘他(tā)更為(wèi)獨特的因素。評論家李敬澤2002年的《半個世紀兩個孫犁》,傳達了同樣的研究旨趣。這一時期,孫犁作(zuò)品的海外譯介情況,亦有(yǒu)變化。
上世紀80年代初,孫犁重回出版界視野。1982年,《荷花(huā)澱》由外文(wén)出版社出版,《孫犁小(xiǎo)說選》由《中(zhōng)國(guó)文(wén)學(xué)》雜志(zhì)社出版。1982年、1983年,《風雲初記》的英文(wén)、法文(wén)版相繼出版。如此看來,孫犁的譯介與寫作(zuò)産(chǎn)生了一個“滞差”:寫作(zuò)進入晚年孫犁階段,但譯介出版的作(zuò)品,仍然是青年孫犁時期的代表作(zuò)。
在研究方面,海外學(xué)者對孫犁的特殊性有(yǒu)了新(xīn)認識。德(dé)國(guó)漢學(xué)家顧彬不再先入為(wèi)主地劃分(fēn)作(zuò)家陣營,對孫犁的評價也随之面貌一新(xīn)。顧彬認為(wèi),孫犁是“解放區(qū)成長(cháng)起來的最重要的作(zuò)家”“甚至是新(xīn)中(zhōng)國(guó)的偉大叙事者之一”“寫出女性戰友們‘美的心靈’”。
稍感遺憾的是,晚年孫犁的作(zuò)品還較少被翻譯出去。很(hěn)多(duō)海外研究者認為(wèi)孫犁的創作(zuò)在上世紀60年代就終結了,這個錯覺也影響了對孫犁的整體(tǐ)判斷。比如Rosemary Maeve Haddond在關于中(zhōng)國(guó)“鄉土小(xiǎo)說”的博士論文(wén)中(zhōng),專辟了“荷花(huā)澱派與孫犁”(Hehuadian school and SunLi)一節,把孫犁置放于鄉土叙事傳統,仍然沿襲了以前的思路。因此,如何重估“晚年孫犁”的價值,将其推介給世界,形成完整的“孫犁形象”,是一個亟須重視的問題。
孫犁青年時,“荷花(huā)澱派”與“山(shān)藥蛋派”相提并論;孫犁晚年時,曾有(yǒu)“南巴(金)北孫(犁)”的說法,由此可(kě)見孫犁的文(wén)壇地位。孫犁崇尚淡泊,自甘“邊緣”,但新(xīn)世紀以來,孫犁研究一直保持着較高熱度,國(guó)内平均每年發表百餘篇學(xué)術論文(wén)。随着國(guó)際學(xué)術文(wén)化交流的進一步增強,相信孫犁的“清荷”“淡菊”風格都會得到海外學(xué)術界的關注,同放異彩。
(作(zuò)者劉衛東,系天津師範大學(xué)文(wén)學(xué)院教授、博士生導師)